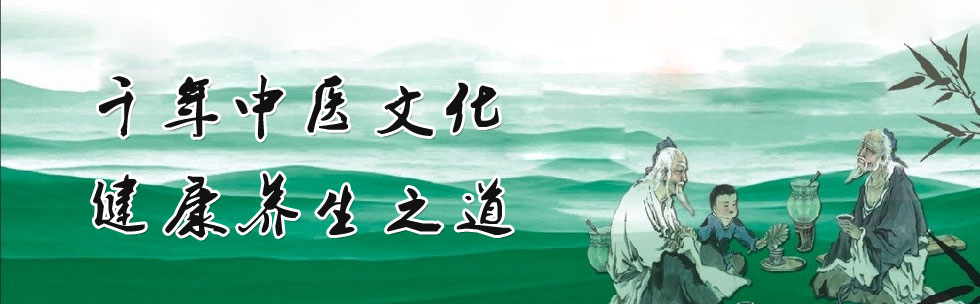|
人杰程仲昭 程家大院,人丁旺者,当属十九世程老三(名开先),生有三子,程仲昭即其长子,下辈达男丁八人,后多单传,二十二世为九人。 “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”(《管子·权修》)。程门历代,都重教育,德行天下,因而名人不断涌现。明正统七年,四世程景方(大院程氏直系亲程景商的堂兄)赈粟千石(相当现在36万斤),被称赈荒义士,明英宗下旨命官府在北街专建牌坊(年该牌坊被迁移至烈士陵园)以彰其功;九世程时建,嘉靖年间举人,任四川成都府通判署知府;十一世程必昇(居老城杨洞巷),于清初即中进士,任山东栖霞知县二十多年,在任期间还始终坚持“闭门读书,不见官长,著有白石堂诗集”;十二世程象辂为清代河南河阴知县;十五世程有觉为清代河南通许知县;十六世程维权(仲昭高祖父),字衡堂,贡生,为人忠厚,以德传家,扶弱济困,邻里有名,“有戚不能蔽风雨,为置房院以居之”,有“无力应试者,必竭力佽助”,“世历五代,书香继续,有登甲科者。福善之极,非偶然也”;十八世程振声(仲昭祖父),字蜚先,贡生,学问扎实,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曾赏识振声文采,欲任用,让他专事教子,而被振声以家母年迈,孝亲难离为由,婉言谢绝。其实,振声既是孝子,也是严父,他严教子孙,也同样是乡里有名的。由于仲昭伯父(啓先)生父(开先)都去世早,仲昭兄弟五人随后凭叔父(际先)一手包揽、资助,而全入正校读书。因际先严管并督导有力,五子皆学业有成,拔萃者有仲昭成为表率,入仕途,政绩显赫,为程门带来了荣耀。 程家大院一代又一代,名人不断涌现,是严教子孙的相应回报。现将近现代,程家大院三辈连出三名人:程仲昭、程小城、程万里的情况,分述于后。 程仲昭(二十世),字朗川,别署“坞樵”,书斋名“艺梅轩”,是“诰赠朝议大夫”程开先的长子,同辈排行老二。生于咸丰八年(戊午),即年农历7月17日(据程仲昭会试朱卷),逝世于年(民国17年,戊辰)农历闰2月19日。 程仲昭在清光绪五年(己卯年)以乡试第十六名考取举人,光绪十五年(己丑年)以会试第一百零七名考取贡士,继以殿试二甲一百二十二名考取进士,初绶安徽霍山县知县,后任安徽盱眙(现在江苏境内)知县,“署巢县署泗州卫守备花翎直隶知州升用知府”。 光绪末年,仲昭弃官归里。宣统二年(年)八月,任韩城县商会首任会长兼盐局总理,直至逝世。年兼任韩城县议会副议长。随后,整理完成《程族八甲分支谱》,以石印告成。年至次年5月,编纂完成《韩城县续志》(后人也称“程志”),该志书于年出版发行。 仲昭一生历经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、民国多个朝代,并身经“百日维新”、“甲午风云”、辛亥革命等世变大事,晚年弃官,为故里效力,促地方发展,以续志问世、文墨丰硕享誉韩原,。仲昭饱经风霜的复杂身世,编织出了他的多采人生,也给后人留下一些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。 程仲昭一生,先后娶妻五房。首妻,乃本地井溢村名门闺秀师氏,虽温良贤惠,但命运多舛,婚后不久因病离世。 随后,仲昭续弦王氏。王氏家与程家是斜对门。当时论富,论门楼之高,王家都在上。所以与王家结亲,曾颇费周折。王氏聪明能干,淳朴中带点泼辣,从性格互补上倒也博得仲昭喜欢。但头次提亲,并不顺利,在王氏眼里觉得,仲昭长相一般,又是家道还不如自家的穷书生,凭什么打动芳心呢。可是仲昭性格内向,有执拗的一面,一心想娶王氏。经三番五次软磨攻心,终于说服了对方。其实,王氏对男方也有中意处,仲昭从小刻苦勤学,品学兼优是周围出了名的,谁不知“从小观大”、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理。王氏心想,仲昭似带官相,嫁给他兴许前程似锦。于是应了婚事。 随后,程家不断加速门第更新,并超过王家,程家终于扬眉吐气了。世间的机缘巧合,矛盾相促,诚然有趣。 新居新婚,双喜临门,程家大院,如日中天。后来长子出生,取名念曾,又名新祎。 婚后有贤妻打理生活,仲昭便一心扑在苦读诗书上。 世无永顺。几年后,却遇年馑,光绪二年因大旱,秋粮薄收,麦未下种。光绪三年,情况更糟,韩原大地,“赤地千里”。光绪四年,韩城“夏粮颗粒未收”,“留人不足十之三”(据市志)。 程家大院老小,在这连年旱灾中,凭着互帮互济,紧衣缩食,苦渡难关。最严重时,同别处一样,也加食“榆树皮、蔺根面”,勉强维生。 仲昭的伯父(啓先)和父亲(开先)未能熬过连年大灾,相继离世。好在仲昭有志,有叔父扶助,荒年未废学业,终于苦学得报,于光绪五年考中举人。 转眼到了光绪十五年,在那面临快要上京迎考的日子,仲昭却总是闷闷不乐。问之,原知并非惧考,只是为经费发愁。说也是,经过连年灾荒,家财腾空,上京赶考,用银缺口很大,怎不犯难。 在此节骨眼上,王氏心生一计,她想到为人仗义的舅父,必可救紧。于是由王氏出面,向吉剑华(本名吉灿升,城内箔子巷人,咸丰年间官至山东泰安府盐运使、按察使)求助,吉剑华答应得倒也爽快。 但是,吉剑华并未当即给钱,而是拐了一个弯儿,他先把甥婿安排在一个安静院落,让其闭门读书,剑华有时也一旁作些辅导、指点,并亲授社交礼仪常识。如此过了一个月左右。然后慷慨施银百两,送他上路,并勉励甥婿沉着迎考。看到內舅如此苦口婆心,指点迷津,大大方方帮助自己,又如此细心安排,其良苦用心何在,聪明的仲昭早已心知肚明。 仲昭多年寒窗苦读,没有白费。光绪十五年(即年),他上京赶考,喜中进士。 程门故事多,先前清代状元王杰(—),曾娶妻程氏,其传说在韩原流传已久,而实事就发生在离古城很近的庙后村,该村程氏就是本族八甲的一部分。 谁曾想到一百多年后,程家大院又冒出了新鲜事:另一段奇缘---程仲昭与袁世凯堂妹袁保龄(清代名臣,先后任内阁中书,官至“二品顶戴”)长女袁世慧结亲的传奇故事。 那是年,已过而立之年刚委官上任的仲昭,有一次去某地看戏,无意中碰到了同时看戏的袁家某人。某人观察仲昭许久,只觉眼前这人很怪:别人是占好位,图看戏痛快,此人却在偏角处对看戏漫不经心,并且身带一书,还时不时地低头翻阅。袁某人便上前问之,原知,这怪人籍非本地,对看异地戏剧兴趣不大,而看书则痴迷成习,已积习难改。这举动倒是打动了那人,只觉眼前这嗜书成癖的怪人,实不多见,愈觉奇遇难得。某人是有意而来,便与仲昭深入沟通,拉远说近,最终鹊桥成事。原来,袁保龄侧室刘氏(封一品太夫人)所生长女袁世慧(长辈称她慧儿)正需觅婿,派人四方打听,这边仲昭的怪相,反而恰成目标。后来,仲昭被引见袁家大人,知根知底后,对方认为比起自家程门虽不十分显赫,但也是书香门第、富庶人家,关键是男方知书达理、前途无量,便提亲酿事。两姓联姻,天作之合,顺顺当当,水到渠成。一切妥善后,两家择了吉日良辰,很快于仲昭任内,在当地隆重地完了婚。 这个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的真实故事,被街谈巷议,一时传为佳话。 天缘作合,世泽流光。仲昭婚后与袁世慧举案齐眉、相敬如宾,日子和谐,生活开心,当年袁世慧喜生一女,取名小翠,长得楚楚动人。令人惋惜的是宝贝命薄,十三岁那年不幸夭折。失去掌上明珠,对仲昭和世慧打击不小,竟成他们终其一生永远也抹不去的一个阴影。 官场离不开文房四宝,徽笔、徽墨、徽纸早已享誉全国,而徽墨更为全国之冠。仲昭正是抓住在当地为官这天时地利之便,而享了多年名墨福。也使他打理案牍、施展文采如虎添翼,为其传世墨迹增色不少。 仲昭使用的仿古名墨,既有使用价值,又有欣赏价值。他的仿古藏墨有光绪十二年崔焕章署名墨、“龙翔凤舞”(圆柱型)墨、“松滋侯”、“艺林珍赏”、名联墨等。这些墨,材质精,工艺细,墨面浮雕图案凹凸有致。有的敷金,光彩富丽。无论墨形或图饰,无不恰到好处,令人赏心悦目。面对这些高级名墨,大概一般人真有奇墨供欣赏珍极不敢用的感觉。 仲昭爱墨若子,收集仿古墨宝是他的特别爱好,他到任后不久,就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农历二月,他曾以官人身份定制了一批精墨,并将“龙门朗川”、“光绪甲午仲春”嘱制于墨锭上。这些墨宝,如影相随,亲密地跟了他一辈子。 盱眙县志有段记载:“高等小学堂官立,在城内宣化坊,就已裁泗州卫署改设,光绪二十九年由知县程仲昭开办。以书院宾兴、卷烛费、旧有田租、滩租等项为常年经费,学生三十六名。”这是仲昭政绩点滴之一,不足为例。他曾任两地(霍山、盱眙)知县,最后官至知府,为官十五年之久,诸多方面已不便考察了。 甲午风云后的中国,民族危机空前严重,导致了随后发生戊戌变法,即“维新变法运动”,虽“百日”而终,但对清政府冲击却不小,从此腐败的满清政府已面临四面楚歌、摇摇欲坠的局面。身为一介小官的仲昭敏感地察觉到前景并不看好,便有了弃官归里的念头,并日益强烈起来。 这一时期,也有想法另类者,韩邑程族八甲的程定邦(十九世,韩城古城南关东侧的庙后村人)也是为人仗义、曾捐款赈灾的乡贤小名人。光绪三十年废止科举后,他独闯南方,曾谋到盱眙候补知县的职缺,但时局动荡,终未入职,后任江苏常州府典史,在外熬过十多年岁月,暮年方归。 人各随心,仲昭可没有乡贤定邦那类一心奔波的意愿,他只慕放翁,心追“坞樵”,一意已决,便在光绪三十四年,毅然解下印绶,辞官返里。 归里谈何容易,那段启程的日子,如何忙迫是可以想见的。仲昭携妻带婢,乘轿雇车,送人运物,好不紧张。有谓:“置家容易搬家难”,何况官家东西多,那贵重用具、文房四宝,加上特产杂品,数千里运程,路遥遥,天长长,日夜兼程,大家一路奔波劳顿。不知走了多少天,终于回到了故里韩城。 回家时,迎接仪式异常隆重。五顶大轿,尊卑有序。袁世慧独为红轿,其他为蓝轿,阵势浩浩荡荡,迎接的、送行的、看热闹的,人山人海,占满了长长的新街巷。在鞭炮齐鸣中,乘轿者,一一落轿,随后徐徐踏毯入门。不同者,唯因袁世慧身份特殊,既是首进者,而且不落轿,专由轿夫抬着直进大门,过扇屏门(平时不开)进院中才落轿,礼遇特别,尊贵可知。 从此,程仲昭身份一变而为地方绅士。有妻室伺候在侧,有婢女端茶送饭,有乡友开始往来,仲昭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,还算安闲自在。 袁世慧是河南项城人,初到新地,多有不惯,听不懂韩城方言,初次还曾闹过笑话。好在她聪慧好问,学中渐知,很快就入乡随俗,融入程家氛围,并因知规懂礼、举止大方、善于理事很快成为人见人爱的熟家人,周围人都尊呼她“袁姑娘”。 此时仲昭长子新祎已临不惑之年。因王氏对独苗的从小溺爱娇惯,任由个性发展,反害了孩子。使新祎养成了公子哥的一些不良习气,以致而立之年而未立,无所作为。仲昭多年在外缠于官场,过问太少,此时也有些自咎。 为了孩子前程,袁世慧出了几千两银子,给新祎捐了一个官,并给足路费,让他出任“九江盐务大使”。岂料,这一招棋也不是好棋。新祎本不是当官的料,也不想进什么衙门,当什么官。一路上心情复杂,精神恍惚,不慎钱物遭盗丢失。眼看无法再上任,他只好原路返回。袁世慧见新祎垂头丧气地回来了,顿觉奇怪,问之,才知原由,还欲继续追问下去,新祎委屈地说:“官场有什么好,父亲都不做官回老家,偏叫我上什么任,是何道理?”一句反驳,倒使袁世慧不好作答,只好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吧。 后来,新祎自觉不可再混日子,就找了收烟酒杂税之类的差事经受锻炼,又雇杨兰亭一旁协助指点,干了一阵子,新祎确有点小进步,能自食其力,家人为之高兴。借此机会,新祎被安排在餐馆当下手,有了新的事干,那一段新祎终于步入正道。 在仲昭所处的封建时代,允许一夫多妻。仲昭在归里后,于年娶扬州大户人家出身的既贤惠又能写善画的方氏为妻。六年后又娶了南方人李氏。后娶的两个夫人,各生一子。方氏之子,即仲昭二儿,取名景曾。李氏所生老三,名述曾。这两个儿子在大院同辈中分别排为老七和老九。 仲昭长子新祎头妻吕氏,死得早,后娶北关杨家女,无子,后又娶薛曲村王氏。仲昭次子景曾,娶妻廉氏(薛庄人)。述曾娶妻党招贤(党家村人)。 宣统元年,清政府借鉴西方一些做法,令各地成立商会,以促经济活跃发展。韩城遵令,经各方努力,于次年八月成立了县商会。程仲昭因系当地知名绅士,又是县商会筹划人,就被选为第一任会长。会址设在古城解家巷。 为符合商会规章精神,在商会成立的同时,在古城南街坐西向东开了个餐馆,起名“福寿园”,后改称“庆寿园”,有韩原小吃,兼带黄酒。程仲昭名义上是餐馆大掌柜,具体操办则由手下人一一完成。 借此机会,新祎被安排在餐馆当下手,有了新的事干,那一段,新祎还算混得人模人样。 由于经验不足,经营吃力,后来庆寿园改由程端甫(新祎二儿)和王鹤亭合作,改名“庆春楼”。后又改名为“重庆楼”,由端甫独办。这算是仲昭过世好多年后的事了。 仲昭的堂弟仲椿(字幹休,二十世中排行老七),也曾于民国十四年和丁家在古城北街合开了“雅气园”,经营炒菜,兼带酒类,后来仲椿因故退出,手续相清后转由丁家独办。再后来,丁家又转让给赵浪亭,赵浪亭又花样翻新,更名为“醉仙居”。 民国时期就是如此,政界斗争激烈,社会复杂,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,商界也似走马灯和万花筒,更来变去,欲稳定从业,那是难上加难。 年,程仲昭兼任韩城县参议会副议长,更添忙碌。 年至年,历时九年,程仲昭完成了续修韩邑程氏谱的工作。他在首谱(程必昇撰于清康熙二十七年)、继谱(十五世程聿候撰于清乾隆十年)的基础上作的第三次续谱(名为《程氏八甲分支谱》,前有“弁言”,后有“跋”,还详列谱别、名宦事迹、功德职官科名录、族贤列传,谱余记录等。这些资料后石印成册,在族中流传。它不仅对研究氏族史很有价值,而且对研究韩城地方史也有一定作用。 年,仲昭受时任韩城知事赵本荫之托担起编撰韩城县续志的重担,从该年10月始修,至年5月完成,次年出书。全书四册,四卷,八万余字。 据老人讲,民国十四年(年),土匪段懋公攻入韩城古城,放抢三天,肆意劫掠,为避横祸,仲昭曾在妻娘家,即斜对门深宅里,躲避过一阵子。 已逾古稀之年的仲昭,受累于连年写作和兵荒马乱之苦,加上家事缠身,健康每况愈下,终于病卧不起,于年(戊辰)农历闰2月19日辞世。这时他已有三子四孙,真是在儿孙满堂中含笑九泉的。 一代德高望重的长者和地方名人过世了,在程家大院,犹如天塌,算最大悲事。由于逝者多年任商会会长,丧事便确定由程家料理而商会参与主持,其隆重之程度,韩原再无先例。为顾及摊子大、客人多,还将起灶和宴请特意设在南营庙内。出殡那日,阵势非凡,送丧犹摆长龙,事大震惊周边,来客有数百之众,光宰猪就十六条,佳肴酒席达几十桌,挽联收到不少,杂礼更是无数。 那时,最吸引眼球者还在正庭,只见幢匾盈宅,礼仪隆重,布置肃穆的灵堂两侧有挽联:“憶昔趋庭闻诗闻礼;於今想像见羹见墙”,寄托哀思,深沉生动。一旁显眼处更有高大的铭旌熠熠生辉,只见中部是庄重的扁宋,书着逝者生前官衔和评辞,旁还署有刘华(进士,三品衔,吏部郎中,湖南岳州知府)大名,原来这铭旌是请衔于名人而特制,实乃礼中之首,压阵尤物。凡吊唁过往者,莫不肃然起敬。 逝者去矣,浩气长存。 虽盖棺论定,仍难免异议。程仲昭同邑、同登甲科老同学吉同鈞,曾作挽联一幅,兼挽兼评,直指遗著:“一手独裁成邑志,千秋事业留后评。”显然,吉对程是敬重的,然而,对其作品—续志,又是不满意的。当然,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地看,有辩证,而不绝对。就仲昭角度,衰年挑重担,既力不从心,又条件太差,时短力薄,压力够大,可是,他仍然作了蚕老丝尽的最后努力,他毕竟交卷了,毕竟填补了韩城历史的一段空白。 年出版的韩城市志,是后世众志成城的杰作,它对续志作了恰当概括:程志“其特点是选材严谨,体例较新”,“尤较前述各志清晰悦目”,“体例较前诸志更臻完善”,总算是一部“体例条目清晰、质量较高的续志”。此乃后评,一个公正论断。 |
当前位置: 传奇 >陕西韩城进士程仲昭朱卷
陕西韩城进士程仲昭朱卷
时间:2023-3-20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yuziys.com/jbby/86545665.html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霸者之刃和命运之刃,这么多年我才知道有隐
- 下一篇文章: 陈赓观察队伍时,和小红军聊了几句,后觉得